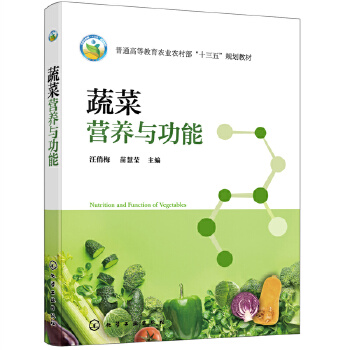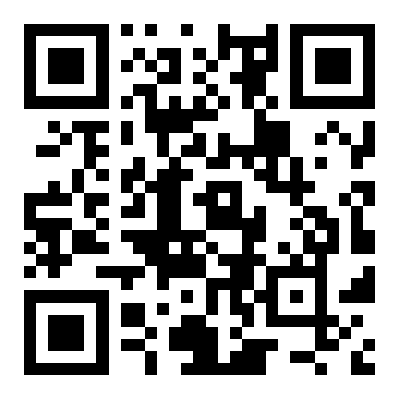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规模持续增加,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2023年自巴西、美国、阿根廷3国进口量占进口总量90%以上;加之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推动大豆进口来源多样化、保证大豆国际供给稳定性意义重大。非洲与我国农业合作机制稳固,种植条件适宜,具备大豆出口的可观潜力。本文从当地生产水平、双边贸易条件、国际合作环境3个维度,剖析非洲大豆进口的可行性和堵点,为拓展大豆进口来源提供参考。
近年来,非洲大豆生产集中于南非、赞比亚、尼日利亚等10余个国家,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3年产量为733.8万吨,与2018年相比年均增长14%。目前,南非、贝宁、多哥等10余个非洲国家有大豆出口,2023年出口规模约为158万吨,其中南非出口量最大,为68.9万吨(表1),主要出口到莫桑比克、印度、巴基斯坦、津巴布韦、斯威士兰。

非洲大豆在加工方面正不断提升。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非洲大豆油产量自2018年的104.5万吨增长到2022年的162.8万吨,埃及和南非是大豆油的主要生产国。豆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家禽业中广泛使用,大豆食品消费也越来越普遍,豆浆和汤是公立学校和医院中营养不良儿童和患者的日常膳食。
非洲的耕地和水热资源丰富,有着较高的大豆增产前景。据FAO和非洲开发银行统计,2022年非洲耕地面积3亿公顷,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03万公顷,世界上65%的未开垦耕地位于非洲,进一步扩展大豆种植规模的空间巨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气温为20~30℃,年降水量为500~2 000毫米,水系丰富,水热条件普遍适宜大豆种植。如日本、巴西、莫桑比克的Pro-Savana项目曾计划在莫桑比克种植大豆等作物,并发现其土壤和气候条件与巴西知名粮食产地塞拉多相似。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FAO预测,到203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油料作物耕地面积将增加7%,进出口活动均将增加。
非洲普遍重视农业发展,多国制定了大豆产业发展促进政策。南非、坦桑尼亚均在国家发展规划类文件中将大豆列为优先或潜力作物。尼日利亚对大豆产业链制定了支持政策,包括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区、出口生产基地和设施、运输设施等,在几内亚大草原区和干旱草原区提高大豆生产力。截至2025年,非洲有11个国家批准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其中南非2001年起种植转基因大豆,占大豆总面积的95%;2018年,尼日利亚批准了5种转基因大豆用于食品和饲料。
在国际合作环境方面,中国对非农业合作历史悠久、形式丰富,为大豆产业合作提供了有利氛围。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对非技术援助;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成立以来,中非农业投资、贸易、援助三大领域逐渐深化。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在非注册农业企业159家,投资存量16.41亿美元。目前,我国进口非洲大豆已有一定的政策和参与主体基础,与埃塞俄比亚(2018年)、贝宁(2020年)、坦桑尼亚(2021年)、南非(2022年)签订大豆输华协议,中粮集团、中纺集团旗下公司、江苏永友粮油经营集团已开展非洲大豆进口。
国际组织在非洲大豆研发、种植方面也给予了大量支持。非洲开发银行2023年发布了40份″国家粮食和农业交付契约″,强调大豆等五种主要作物的重要性,将通过大规模种植和工业化提高产量;2024年向尼日利亚投资1.34亿美元支持其5万公顷大豆以及其他作物的大规模种植。FAO通过″一国一品″项目将大豆定为加纳和津巴布韦特色农产品,开展对农户、大豆加工商和餐饮供应商的培训。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开发的适合非洲的大豆品种使其平均产量在30年间提高了67%。
非洲大豆生产水平仍受农业投入、基础设施、加工条件制约。非洲大豆种植以小农为主,约90%的大豆种植农场面积不到5公顷,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不足;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公顷杀虫剂使用量仅为0.7千克(低于世界平均2.4千克),且属于化肥净进口国,受近年来化肥进口成本上涨的限制;大豆烘干、筛选等服务设施落后,缺少大豆加工企业,基本由饲料和家禽生产商垂直整合进行加工;产地到港口的公路运输设施条件差、成本高。
非洲与我国的大豆输华协议签订时间较晚,其他双边协定范围有限。目前,我国仅在2018—2022年与非洲四个国家签订了大豆输华协议,与少部分非洲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部分输华产品免关税待遇(表2)。因而中非大豆贸易的初始贸易规模小、贸易时段更晚,拓展贸易的基础水平较为薄弱,对后续维持长期贸易关系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在贸易运输条件上,非洲农产品进口面临物流通道不畅的问题,如中非海运航线数量较少、频次低、耗时长,港口货物滞留时间长,非大豆收获季物流设施和配套人力闲置。据了解,美国、巴西大豆运往国内需25~50天,贝宁运往国内则需要45~65天。中非农产品运输的时间成本较高对企业的投入和积极性均会造成影响。
欧美国家借援助项目进行生产技术研究和培训,提升非洲大豆产能、培育需求。自201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领导的保障未来粮食供给项目推出大豆创新实验室,覆盖31个非洲国家,涉足大豆品种试验和育种、病虫害、机械化、大豆消费和营养等,致力于推广符合其大豆生产标准的技术并将此类大豆产品推向非洲市场。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农业贸易促进计划支持的尼日利亚大豆卓越中心提供了家禽生产、饲料加工培训。德国发起、欧盟和瑞士共同出资建设了16个农业和食品行业绿色创新中心,其中多哥、贝宁、赞比亚、马拉维4个非洲中心涉及大豆。
国际粮商、种企已长期在非运营大豆加工销售业务,引领转基因育种。路易达孚在南非设立办事处已有百年之久,持续开展大豆和豆粕等农产品分销和进出口。嘉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埃及的油籽行业,持股国家植物油公司比例曾高达98%,2015年投资1亿美元促进在埃及大豆油压榨业务产能翻倍,并收购赞比亚卢萨卡的大豆压榨、炼油厂和装瓶企业;2018年,与ADM在埃及成立大豆合资企业,运营埃及国家植物油公司的大豆压榨设施。截至2025年,南非已经批准种植7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其中5种由孟山都、巴斯夫、拜耳、陶氏益农等欧美种企研发。
非洲有着较强的大豆产业发展前景,其生产自然条件优越、产量和种植面积均呈上升趋势且有较大上涨空间,出台了积极的大豆产业政策,同我国有着坚实的农业合作关系、具备一定的大豆贸易基础。但同时,非洲大豆产业发展仍受到农业加工、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限制,同我国的贸易优惠政策和大豆输华协定范围较窄,欧美国家和国际粮商已在其产业链条上有所布局,需抓住时机深化中非大豆产业合作,协助其改善生产条件、提升出口能力。
一是将中非大豆产业合作纳入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工作任务进行系统研究谋划。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平台作用,联合相关部门以及国内大豆产业中的大型种植生产、贸易流通、农资服务企业及金融机构进行充分研究,确定合作框架、目标、路径和时间安排,改善当地大豆生产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不足的现状,显著提升合作国投资环境。
二是推动与重点国家就大豆全产业链合作深度沟通。在中非农业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落实《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与重点国家进行意向沟通,协调土地、开发模式、支持政策、技术交流等问题,早日形成合作共识,深度布局种子农资供应、土地开发种植、产品回运通道全产业链合作事项。
三是布局建设中非大豆产业交流合作系列平台。利用我国已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援助项目及涉农企业境外投资园区等平台,建设中非大豆技术研发中心、产业园或示范培训基地,与非洲大豆研究机构和商协会等开展品种、技术、设备、仓储运输等交流合作,促进形成中非大豆技术和产业互促互进合作态势,为拓展中国大豆进口来源提供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