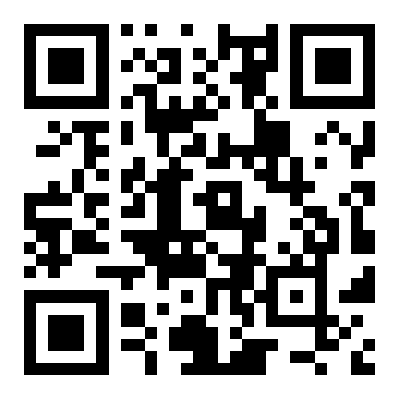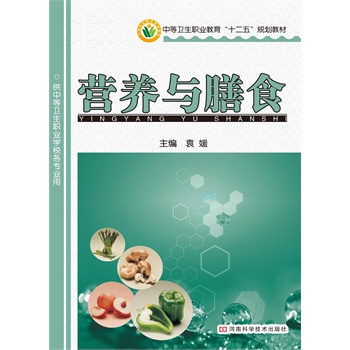
》时,我已经回国两周重回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了,但并没有中断和美国那边朋友的联系,直到今天仍然跨着12小时时差保持联络。
当时在美国那边接待我的是我母亲的多位同学,我从小就与这些叔叔阿姨关系熟络,他们如今都已经移民美国近30年。我自己也有许多正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旅行中也安排了见面。
在差不多15天的时间里,我和在美国拥有不同生活状态、也处在不同身份状态的中国人/华裔对话交流。他们有的已经完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多年,有的虽然只拿了永居权但已经自我定义为“美国人”,有的在朝令夕改的签证政策中等待一纸决定命令的“门票”,还有的面对趋于饱和的美国社会仍在犹豫是去是留...
整个旅程中主要陪伴我的是一对夫妻,Jolie和Saul。他们和我母亲同样的年龄,妻子是马萨诸塞州一家赫赫有名的生物医药公司高管,丈夫是全职先生。两人过着在美国不算罕见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生活,年收入不菲,在当地属于富裕阶层。
在Jolie和Saul家做客时的合影,他们几乎每顿饭都用高级昂贵的饭菜款待。
他们是在90年代中后期移民来美的。这个时间也是大多数上一辈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高峰期——当时正值国内的第二波“出海/移民潮”,国内环境相对也处于“动荡期”。
11.5万个签证名额是什么概念?H-1B签证年度上限(Annual Cap)是老布什总统在《1990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90)中设立的,当时规定每年6.5万签证上限。所以98年的法案相当于将该数字加了近乎一半,在后来的2001-2003财年,国会甚至将上限提升至19.5万注,整整比10年前翻了三倍。
那个年头正巧赶上美国和全世界经济兴荣、高科技行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公司声称面临技术短缺难题,这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等高端技术领域尤为明显。吸引并留住高技能外国工人的需求一度旺盛,H-1B大量发放的政策因而问世。虽然后来该法案争议高涨,导致2004财年政策突然断崖式紧缩,但许多华裔都是在21世纪前后的几年盯住机遇吃上了移民红利。Jolie和Saul身边的绝大多数也都是那个时候办妥了移民。
对于这些在20世纪80-90年代抵达美国的一代移民来说,他们的大多数最初都是被民主党吸引而去。这不完全是因为克林顿本人或政府,更是当时民主党整体倡导的友好亲和的移民权利和对少数族裔的优厚包容,贴合了他们的切身需求——就业机会、医疗保健、子女教育支持,以及最重要的东西,绿卡。
在这些一代亚裔移民眼中,80、90年代的民主党就是“自由的灯塔”,被包容的感觉处处温存。另一边,共和党政客经常忽视亚裔移民,尤其对华裔来说,他们常常被简化归类到关于中国或所谓“外部威胁”的偏激叙事中去。虽然民主党所鼓励的“文化多元”对亚裔群体来说在移民事宜的考量中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他们当然更关注切实的物质利益,但在初入一个陌生而备受排挤的社会空间时,这种情绪价值也尤为珍贵。
但就是这一代亚裔移民,在他们在美国生活成长的二三十年间,发生了很明显的“右化”倾向,华裔移民对此最为凸显。观察美国政治社会变迁的学域对此几乎达成共识,而对其中缘由的猜测参差不齐。我记得从2020年开始,每到大选周期,亲民主党媒体《纽约时报》就瞄准了亚裔/华裔,不断推出针对这一群体的分析文章,因为在2020年大选中亚裔选民右倾化的状态已经达到高潮。
Jolie也告诉我,自从获得公民选举权后,她虽然主观上并没有特意支持某个党派,但承认自己大体上“原先是中间偏左,现在是中间偏右”,而且她身边的移民朋友大多和她持相似的态度。那这种转变从何时开始发生?Jolie无法指认出一个具体时间,但我的推断是大约在奥巴马时期发生。
从着手置办移民事务开始,Jolie和Saul大概经历了6届美国政府。对于其中早期几届,他们无论党派都是偏于积极的评价:“来美国之前觉得里根还不错,对世界格局影响很大,而且不极端;克林顿对我们移民很友善,相对来说举止也儒雅风度;小布什虽说没有他爸爸的气度,但也挺有水平,9/11的时候处理得还算合格。”
话锋在说到奥巴马的时候急转直下。他们总是面红耳赤地用“邪恶”“狡诈”“虚伪”“胡来”,这些黑暗词汇堆砌对奥巴马政府的评价,有时也顺带着把拜登一顿株连诟病,不掩饰也不忌讳言语“恶毒”。为什么偏偏如此痛恨奥巴马?有两件事被格外提到。一个是当年令他们咬牙切齿的医改法案。在像他们这样的高收入群体眼中,民主党后来任何所谓的“社会福利”都是败坏真理的可笑滥话。拿医改法案来说,“真正的医疗福利从不存在,是我们纳税人的钱白白送给不三不四的人吸毒打针去了”。
Jolie和Saul在提到往届政府时一向言语温和,唯有对奥巴马咬牙切齿,甚至会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描述他。图片拍摄于费城美国宪法中心内的商店
还有一件事是“营养午餐计划”。当年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提出了这项旨在提高政府支出给中小学生发放健康午餐的政策,“但是小孩就喜欢喝可乐吃炸薯条,不爱吃所谓营养餐,午餐后来全都浪费了,但那些午餐钱哪里来的?不都是从我们纳税人的钱包掏的吗?”
“民主党掠走了我们纳税人的钱”,是我在同Jolie和Saul所有交流中最常听到的话。绝大多数华裔在最一开始选择去到美国的时候,动机只是最基本朴素的愿望:拿到漂亮的bill,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凡拿到绿卡的都算是移民既得利益者,那些成功跻身上流的更是“王中王”,三十年间赚着比人民币高出几倍的美金安逸度日。三十年前为拥有和美国人一样的权利资格激动不已,三十年后心态早已从“成为美国人”潜移默化到“是美国人”。
正因如此,近几年新引入的移民并不是“移民”,而是“外来者”,其中那些低素质的人正在“入侵”自己的家园,打破他们的美好生活,毒品肆虐流通、空气质量恶臭、“奇形怪状”的人不断涌现、无能之人靠政府没有原则的补助得意生活——而这一切的原罪就是当初给他们带去移民红利的民主党。
他们更是对当下“白左”的极端价值观失望愤怒。初代华裔移民尽管很多源自文化保守的中国社会,但思想和价值观在美国浸染多年,对性少数群体大体上是包容开放的。但这不等于能够接受过分荒谬的性泛滥。在Jolie这一代人眼中,今天的“白左之风”已经变得邪恶扭曲,社会道德糜烂沦丧,甚至已经没有起码的秩序可言,这一切也是当初给他们提供了“干净的情绪价值”的民主党造成的。
特朗普出现之后,声称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承认“美国只有男与女两种性别”、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切反而非常符合那些初代亚裔移民的需求,他们似乎重新看到了几十年前自己刚刚来到美国时的理想愿景。民主党激进失控的平权政策造成了无法容忍的破坏力,特朗普煽动性的种族主义没有招致反感,反而像一股“拯救圣光”倍受拥戴。
Saul告诉我,这一代华裔设身处地地目睹了美国政治风气的变革。在他们眼里,以前民主党代表着社会底层,共和党代表着上流人士;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民主党成了精英派,而代表平民大众的反倒是共和党——所以“有良知的人都会支持共和党,只有虚伪愚蠢的人才会支持民主党”。但我认为真正的解读应该是,与其说他们支持共和党,不如说他们需要特朗普;与其说他们需要特朗普,不如说是实在厌倦了民主党。
这种感觉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去年英国大选时我问我的英国朋友们“为什么都选了斯塔默”一样。他们的回答是,并不是支持斯塔默,甚至有时都不太关注他的具体主张,只是对保守党感到疲惫了。同样我还想到了今年年初移民多伦多的朋友对特鲁多的评价,“反正总理只要不是他就行。”——现在欧美社会都一样,都在盛行这种“比烂之风”。
我在这次旅行中还约见了几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我高中时的同桌Tia,我们至今都联系密切。Tia本科时在国内一所985大学学习医药专业,2022年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读研究生,学习的是生物技术专业。这个专业如今的敏感程度并不亚于STEM。我记得Tia三年前申请研究生项目的时候来找我咨询过留学经验,当时我劝她考虑德国留学,因为那里的药学实力强大,发展潜力在世界也属不错,但她最终选择了美国,其中最大的目的就是永居。
在宾大与Tia边散步边聊天时拍下了沃顿商学院,但遗憾的是忘记在她所属的药学院合影留念。
Tia的导师是一位大她几岁的华裔。这些年常春藤高校一直是特朗普的“眼中钉”,宾大去年因为被特别针对也多少闹得人心惶惶,更何况生物医药行业这两年还面临着资金短缺问题。特朗普政府如今削减了对NIH(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金的投入,导致学校的项目和实验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已经有一些开始裁员。
即便如此,她的导师却对特朗普再次就任感到无比欣喜,理由是“行业门槛因为政策而拔高,收到的学生简历比以往的质量高出不少。”——其实很明显这个理由是肤浅之谈。Tia的导师在宾大拥有一份稳定的助理教授职务,社会地位至少属于中上游,本职工作加上额外项目下收入可观,更重要的是在去年顺利办下了绿卡。
所以更深层的内核是,这些年的“新一代移民”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既得利益者”,他们非常想看到政府出台更强硬的移民限制,从而让政策围墙圈护住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至于共情于尚未移民的华裔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历史总是在反复,这与上一代移民如出一辙。
而像Tia一样的新待移民者,则成为了迷茫的下一代,在随机与偶然中无限等待。虽然哈佛的事情出了后她没有过分紧张,几年下来对这样的新闻早就习以为常,但签证问题是躲不过的大山,这两年的阻碍更是厚重。政府越来越对STEM专业F-1签证和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OPT是对在美国持有F-1学生身份的国际学生获得实际工作经验的许可项目,类似于实习机会)过度关注。以往STEM专业的F-1签证虽然会有较长的审核期,但终究会给下来,而现在却随时都有被拒的风险。
更何况,“行业门槛因为政策而拔高”对导师来说或许无伤大雅、有利有弊,但对像Tia这样没有太多背景与资本的人来说,前方是僧多粥少的无奈,还有随时被淘汰的危机。她身边的同僚和学长最初来美求学时和她人生规划相同,但都在这两年开始考虑离开,有的人已经着手规划转去欧洲、新加坡或中国香港学习,甚至很多打拼多年的博士后也开始考虑回国,卷入就业市场也差不多饱和的教职行业寻求工作。
理论上讲,他们的履历都闪光发亮,都是有资格去全球数一数二的顶尖事务所/学府深造谋职,但没有定数的签证政策消磨了他们的耐心和热情——原先只是走个程序的东西,如今却成了一堵高不可攀的沉重围墙。
今天的华裔移民,在自由与秩序、身份与利益、共情与自保之间游走。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也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成为某种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从争取留下来的那一刻起,很多人就已被卷入一场关于归属、安全与代价的长期博弈。当“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适应规则”的本能,人们也悄然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这并不意味着背叛初衷,而是在复杂现实中的一种本能回应。而这份回应,也正悄悄塑造着今天的美国。